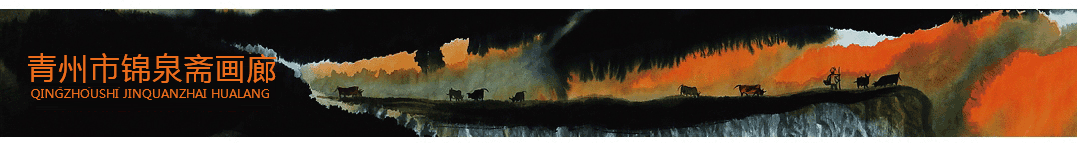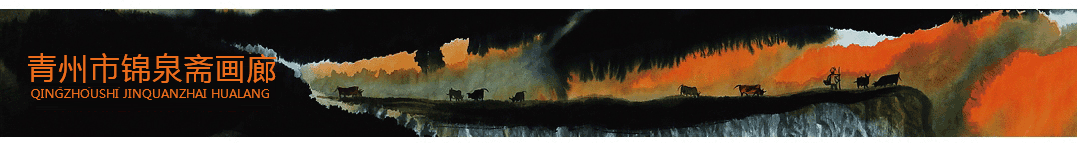中国书画艺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遗产丰厚。它的生存、发展、兴衰、演变、一直受到文化、科技、政治、经济、教育以及自然、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中国画艺术在过去、现在所发生的任何现象,往往都具有复杂的内因与外因,其昔日的、未来的演变与发展都始终贯穿着自身的规律性。
当代社会的每一位公民都可以依据其文化权力,基于各自的审美习惯与偏爱及其修养水准,按个人意志作出不同的艺术选择,发表不同的艺术见解。但是,任何人、任何单位(无论是平民百姓或名人权贵、业余爱好者或##研究者、民间组织或官方机构)面对中国画作品的认证备案、真伪鉴定、优劣评论、学术定位、价值评估等##问题,都应以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力求认知的##性、系统性,##策略与计划的合理性、可行性,而绝不可受个别人或个别单位、个别##的主观意志与利益之驱动。中国画艺术研究是一门学科,中国画艺术管理是一项##,中国画艺术事业需要科学发展观引导。当代中国画艺术发展与繁荣的局面,不是仅凭热情和干劲就可以迎来的。为此,中国画艺术的创作者、收藏者、管理者以及热爱中国画艺术的大众,都要以敬畏艺术的心态,遵循##认知、理性思维的学术原则,##认知中国画的画种特点和形态架构,及其诞生、优化、传承、演变的规律性;并针对当下中国画创作、研究、宣传、交流、交易、收藏等方面的认知缺失与管理混乱等问题,认真探讨中国画辨伪、防伪的方法与策略及其学术价值、市场价值的评估准则与体系;并探讨如何建构中国画管理体系,抵制学术腐败,改善艺术生态环境,推动中国画艺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的路径与策略。从中国画艺术的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入手,可以让我们更##更##地了解中国画艺术。
关键词:画种优化 ##认知 理性思维 科学管理 多元发展
引言
中国画艺术进入20世纪后,其赖以生存的文人贵族圈伴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消亡了,它却在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大变革时期,有幸步入了当代社会的大众艺术圈。中国画艺术经过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裂变,蜕变,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逐步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涌现出诸多名师佳作,铸就了这一画种的空前发展与繁荣。而今的中国画已伸延到了当代社会的各个空间,成为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参与在精神文明的架构之中,而且进入了投资、收藏、交易的价值系统和商业领域。这##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同时也是一件让人操心的事。因为有众多投机者跨过了中国画绘制、宣传、经营的“低门槛”,并力图在搅混其水之后追名逐利。炒作“画家”、炒作“画派”的伪劣艺术活动大量涌现,伪劣的中国画画家及其伪劣的中国画作品已泛滥成灾。发生在中国画领域中的学术腐败现象和市场欺诈行为,日积月累,愈演愈烈,已成为当代画坛之重病,严重影响到中国画的整体形象!既然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一种艺术,触及到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及物质利益,那么就应该让更多的人更##地了解它,我们既要看到辉煌业绩的一面,又要正视乱象丛生的一面,对其历史与现状进行##的观察,力求##认知,并在理性思维的轨道上推动其发展与繁荣。
当我们步入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场所或某一个区域,往往会看到“入园须知”、“参观须知”、“乘客须知” ……生活在当代文明社会的任何人,都将面对着诸多陌生空间或领域,都需要辅以“须知”,并启发其“须思”。在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中国画神圣的艺术殿堂或进入其混乱的艺术市场之际,此文将呈上关于中国画艺术的“须知”与“须思”。
一、 关于中国画画种培育者的“须知”与“须思”
中国画被称作一个画种早已是既定事实,但这一画种的发明者是何人?培育者是何人?其研究脉胳尚存在缺失。
决定一个画种客观存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是特有的绘画材料与绘画方式,以及采用此材料、运用此方式创作出来的有别于其他画种的一系列作品。也就是说,这种绘画材料与绘画方式的发明人以及##早以此进行创作实践的艺术家,便应是此画种的培育者。若能将这些发明者的科研过程和相关艺术家的创作历程考证清楚,该画种的培育情况也就会清晰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许多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想考证一个画种的诞生过程绝非易事。在人类的自然科学##,各类科学技术发明往往会有较具体的初步构想以及雏形产品,甚至会呈现出较清晰的标志性发明人。而画种之发明之培育之优化,或者说绘画材料与方式的更新,往往是在原有材料、原用方式的基础上众人参与,逐步改造,不断优化,经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才逐步形成的。尤其是在文明程度不高的古代社会,既没有研究绘画的##人员,又没有专门研究美术历史并及时为之备案的专家与机构,中国画科研与创作的诸多历史信息,早已伴随着历史烟云消失地无影无踪了。
尼德兰画家凡·艾克兄弟于15世纪初期##运用自己试验成功的鲜丽油画色,为根特市圣贝文教堂创作了三叶式祭坛画《根特祭坛画》。这是标志着油画艺术诞生的一件作品,但并不意味着构建油画艺术的全部因素都由此作发端。此作从素描、色彩、构图、造型以及人物形象与性格刻画都十分成功,技巧娴熟,功力深厚。显然,凡·艾克兄弟发明并采用油画新材料之前就已有了相近的绘画方式及材料,《根特祭坛画》背后所蕴藏的艺术传统,绝非凡·艾克兄弟一代人或再上溯几代人的绘画实践就可形成的。所以,油画艺术的培育者不可能只定位在某项材料发明人及##采用新材料的个别艺术家身上。凡·艾克兄弟作古已600多年了,尼德兰作为##也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了,但是油画艺术的材料科研和艺术创作一直在继续,由尼德兰漫延到了欧洲各国、世界各地,逐步成为世界公认的大画种。
中国画虽然诞生得很早,但是得其名却较晚。学者们曾根据历史文献考证中国画得名,目前查找到##早连用“中国画”三字的出处是明顾起元《客座赘语》,意大利传教士、学者利玛窦言及中国的画和意大利的画时曾言:“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凸凹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显然,利玛窦此言中的“中国画”尚不是表述一个画种所用的##名词,所表述的仅是“中国的画”之意。20世纪初,中国开始有了模仿西方美术教育模式的美术学校,其教授课目中有了“洋画”、“国画”之称。同时也由于国外的油画、版画、日本画等画种纷纷传入中国,为了与之区别便逐步叫响了“国画”与“中国画”。1957年,周恩来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上表态,认为“国画”的称谓不妥,提议使用“中国画”之名称,于是“中国画”之名才被美术界以及全社会普遍接受,“国画”则作为简称也被社会广泛采用。由此可见,“中国画”之名被广泛使用仅仅是上个世纪的事,但是在未用“中国画”名称之前叫“画”的历史岂止千年。此类起源于中国的画,作为一个画种并以“中国画”为名,与油画、版画、水彩画等画种相对应,显然存在一定问题,并早在学术界存有争议。但这不是此文要探讨的内容,所以恕不在此赘述。那么,中国画是于何年代怎样培育出来的呢?它是怎样伴随历史进程而不断优化至今的呢?能否紧紧围绕中国画这一画种的诞生与演变,呈现出一个较##、较完整的中国画艺术谱系(包括材料与技法、画家与作品、风格与流派各子系统)呢?为此,我于三年前便组织了该项研究的##团队,虽然在汇编美术文献及考古资料的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随着研究的展开及深入,显现出来的残缺和暴露出来的疑点越来越多,甚至越研究越感到距离结题目标越遥远。我经常围绕这项工作与一些##的中国画创作者、研究者交谈,却发现在这些##人士中也有许多人对中国画缺乏正确认知。有一些人在高谈阔论中国画时常常会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中国画艺术……”这已是当下颇为流行的一句“行话”了,但我要提醒人们,这华而不实的语句中存在偏见及误导,须知此言略去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同时值得大家须思的是,某种文化培育了某个画种的观点,是否是具有学术支撑的##认知?
中国画这一画种的培育过程及其不断优化的漫长历程,始终贯穿着科技发明与艺术创新的相互融合、相互支撑。中国画(包括绢本、纸本等载体上的工笔画、水墨画)所用的工具(包括毛笔、毡等)、材料(包括墨、色、纸、绢等)和托裱工艺,都是决定其成为一个画种的重要因素。这些工具、材料和工艺的发明人,均是培育中国画这个画种的群体团队中不可或缺的成员。虽然这些昔日的发明在今人眼中技术含量并不高,技术难度也不大,甚至会被某些人认为不足挂齿;然而就是这些不起眼的科研成果集结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画的基本样式与特征,使其不仅成为一个画种,而且是在艺术特色和表现力方面具有一定优越性的一个画种。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的笔、墨、纸、绢等绘画工具材料之发明与更新,就无法形成中国画独特的绘画方式与样式,何谈中国画的民族风格、美学特色、独特的艺术体系?又如何能与世界美术大家庭中的其他画种“拉开距离”?怎能有中国画昔日之辉煌与##之繁荣?由此须知:中国画这个画种,是众多不知名的发明人与众多知名的艺术家共同缔造的,是与之相关的科研活动及其艺术实践共同培育的,是文化与科技成功融合的产物。中国画##群体为这一画种确立了##的绘画材质与方式,并在漫长的创作实践与科研创新中对其不断优化。使其超越了描摹物象之识,在追求理、趣、意、韵的层面,艺术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中国画艺术更加特点鲜明、优点突出。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在中国画认知方面缺乏科学观念与学科意识,旧文人与官僚们视中国画为供皇室宫廷、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们把玩的“玩物”。中国画创作者被视为艺人,而那些发明制作笔、墨、纸、绢的人则是小手工艺者,在世人眼中充其量是些匠人,社会地位更为低下。受此传统观念影响,现当代出版的一些论著中依然忽视中国画缔造过程中的科研作用及其群体贡献。曾有文章把唐代画家王维称之为“水墨画之父”。王维作画利用了水墨材质的特性,改单线平涂的画法为墨色深浅层次的画法,以求水墨浓淡渐变相互渗透的效果,创“渲淡法”,创“泼墨山水”,确实功不可没。但是王维之法仅是中国画创作领域中的一类绘画方式的一种技术性突破, “水墨画之父”仅可作为后人对于王维的一种美誉,开创水墨画这一画种之荣誉不是他一人所承受得起的。在此,我并不想否定或者降低王维在中国美术##的重要地位,而是以此为例告人须知,不要以较早较有影响力的一位艺术家创作实践取代一个画种的科发团队及科研历程。
画种如同艺术之舟,画家是艺术之舟的驾驶者。艺术之舟的诞生需要有绘画材料与绘画方式等各环节的发明与设计,缺一不可。中国画材料的发明者和将其材料应用于中国画的设计者,以及每个作出贡献的参与者都是中国画艺术之舟的##。然而,我们在整理中国画艺术谱系的工作中,查阅了中国美术史著作的诸多版本,却从中找不到这些##的身影,仅有的是中国画之舟的诸多“驾驶者”及其笔下的不朽之作。这样的艺术史观察是不够客观的,其学术架构必然是不够坚实的,这正是艺术史学科中有待补充的一个遗憾!
中国书画艺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遗产丰厚。它的生存、发展、兴衰、演变、一直受到文化、科技、政治、经济、教育以及自然、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中国画艺术在过去、现在所发生的任何现象,往往都具有复杂的内因与外因,其昔日的、未来的演变与发展都始终贯穿着自身的规律性。
当代社会的每一位公民都可以依据其文化权力,基于各自的审美习惯与偏爱及其修养水准,按个人意志作出不同的艺术选择,发表不同的艺术见解。但是,任何人、任何单位(无论是平民百姓或名人权贵、业余爱好者或##研究者、民间组织或官方机构)面对中国画作品的认证备案、真伪鉴定、优劣评论、学术定位、价值评估等##问题,都应以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力求认知的##性、系统性,##策略与计划的合理性、可行性,而绝不可受个别人或个别单位、个别##的主观意志与利益之驱动。中国画艺术研究是一门学科,中国画艺术管理是一项##,中国画艺术事业需要科学发展观引导。当代中国画艺术发展与繁荣的局面,不是仅凭热情和干劲就可以迎来的。为此,中国画艺术的创作者、收藏者、管理者以及热爱中国画艺术的大众,都要以敬畏艺术的心态,遵循##认知、理性思维的学术原则,##认知中国画的画种特点和形态架构,及其诞生、优化、传承、演变的规律性;并针对当下中国画创作、研究、宣传、交流、交易、收藏等方面的认知缺失与管理混乱等问题,认真探讨中国画辨伪、防伪的方法与策略及其学术价值、市场价值的评估准则与体系;并探讨如何建构中国画管理体系,抵制学术腐败,改善艺术生态环境,推动中国画艺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的路径与策略。从中国画艺术的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入手,可以让我们更##更##地了解中国画艺术。
关键词:画种优化 ##认知 理性思维 科学管理 多元发展
六、中国画作品真伪方面的“须知”与“须思”
很久以前就有了中国画作伪者,我曾试图考证中国画的##个赝品制造者和##个真伪鉴定者,但由于历史的某些脚步是##迹的,仅凭尚存的历史文献不能##查清,所以至今对这两个##不敢断言。其实,没有必要急于考证中国画造伪与辨伪的历史起点,能否考证##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了解中国画真伪之间的较量过程,正确认知中国画鉴藏的历史。
宋代初期之前的中国画临、摹、仿行为多数是为了学艺,或者为了作品的传播与传世,恶意制造中国画赝品者较少。因而发生在中国画临本、摹本、仿品与鉴藏活动之间的道德冲突、利益冲突较少,真伪之间的较量也较少。自明中期开始,以“苏州片”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画作伪业开始泛滥。临、摹、仿、造、改、配、添、代种种手段兼用,并由个体作伪演变为分工绘制,作坊生产,商业销售。于是,中国画作伪由此开始愈演愈烈,中国画真伪之间的较量不断升级,逐步社会化了。真伪双方的对抗性越来越明显,欺诈与反欺诈的斗争越来越多,反复进行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争斗。在中国画真伪之间的不断较量过程中,鉴定工作者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中国画经验鉴定系统,也称之为“眼学”。当然,尚不可称其为中国画鉴定学,虽然也曾有人力图将以“眼学”为主体的中国画经验鉴定##提升到学科层面,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经验积累到建立学科,还需要有更多学术支撑和更完备的知识结构。特别是面对中国画真伪这个错综复杂的千古难题,所有研究者都必须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专家曾于20世纪80年代巡回全国各博物馆、图书馆、大专院校、文物商店,共同鉴定了数万件古代书画藏品。他们对其中的部分作品真伪虽然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并没有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去统一意见,而是将每个人对每件作品的不同意见都记录下来。我曾见到一份针对235件元代以前作品汇集成的表格式资料,题名为“元以前传世书画作品专家不同意见”,并在表后说明:“以上只是就手中的资料简略的列表,便于浏览。从中可以看到对元以前书画鉴别,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见解,可知这中间存在的难度。工作艰巨,有待继续克服,更有望于来者不断攻关。表中对国外收藏古书画的小部分,附加了一点意见:所有国内外私人藏品不在此列,表中各家意见,仅供参考,不能作为结论。特此申述拙见,伫候各方专家、读者有以教之。”老专家们的求实态度确实令人敬佩。
中国画经验鉴定体系有点像当年的郎中,望、闻、问、切,凭直觉、靠经验诊断病情,其结果难免出问题。现代医学带来了全新的知识结构,更多的诊断****方法,中西医相结合便成了我国医学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往的中国画鉴定者主要靠经验,鉴定##杨仁恺曾说:“鉴定的本质是经验。”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经验的作用是有限的,有时候仅凭经验办事会导致失误。杨仁恺的书画鉴定经验非常丰富,很难有人可与其相比,可是,他却在“河南石鲁假画案”中看走了眼,当时看走眼的还有其他几位专家和收藏者。这个制售石鲁假画多达千幅的大案被河南警方成功破案,对中国画经验鉴定系统无疑是##重创。此案造假售假的那几位涉案人员,若与当今的中国画造假售假高手比,还算不上正真的高手。何况杨仁恺还是石鲁先生的同乡好友,他对石鲁其人其画颇有研究,颇有经验。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几位专家的“走麦城”,否定他们的一生业绩与英明,但正是这类靠经验导致失误的教训,使中国画鉴定工作者开始反思。中国画鉴定过程应像司法破案过程一样,要注重证据。取证的成败往往决定了破案或鉴定的成败。所以,“科学取证”应是中国书画鉴定工作的重中之重。每一位书画鉴定工作者都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为此,我们曾以“科学取证”的理论与案例,与一些中国画鉴定专家共同研究探讨中国画鉴定观念问题,后来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画鉴定的未来之路,一定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要尽早创建成熟完善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体系。目前,关于中国画鉴定的书籍已经出版了许多种,其内容大都是一些经验总结和案例分析。中国画鉴定研究者的视野一直受历史条件所局限,迈向学科建设的科研条件一直不够成熟。杨仁恺著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曾力图将中国书画鉴定##由经验积累的层面推向更高的学科建设层面,虽然这部书在理论设计方案和学术观念方面都存在不足,但是这部十多年前问世的书无疑是当时中国书画鉴定##的##之作。杨仁恺在此书中将书画鉴定的种种方法概括为四个字:“科学论证。”由此可见,他想让中国书画鉴定##由“经验+直觉”的层面向“科学论证”的层面转换与提升。当然,他的这个美好愿望无法在传统鉴定模式中实现,反而会使人们在其转换与提升过程中逐步觉悟:鉴定的本质是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而不是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科学论证”高仿级的中国画赝品是危险的,是难免出错的。“科学论证”的前提或基础是“科学取证”,而中国画鉴定的科学取证之“证”,往往来自绘画材料方面的微观物证,而且这种微观物证常常具有无可争议令人信服的特点。传统的中国画鉴定在从艺术风格与绘画功力方面进行鉴定分析时,常会因笔墨的偶然性及作者风格、水平的不稳定性而感到困惑,甚至导致失误。所以我认为,中国画鉴定的途径不能仅在中国画作品的艺术形态领域,必须进入物质形态领域,以现代光学仪器无损伤地检测中国画作品的纸、墨、色、印迹的物质成分和微观形态,再将其检测数据与数据库中的各种备案数据进行比对,是识别中国画真伪的重要途径。
中国书画纸历史悠久,在造纸工艺、原料成分、品种样式诸方面,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区别,又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有着许多随时空变化而产生的特征与规律。分析不同年代不同种类的中国画纸,捕捉其规律性特征,可以成为鉴定中国画作品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画的色墨品种也十分丰富,各有其时代烙印和规律性特征。特别是中国画用色,有矿物质颜料、植物颜料、化学颜料三大类,有诸多品种与品牌。检测各类颜料的不同成分,研究其产地、起用时间,也是鉴定中国画作品的一条重要途径。用印是中国书画一大特色,各类印章和所用印泥品种也十分丰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印泥。印泥盖在书画作品上,其印色将贴附着书画纸纤维渗透和蔓延。检测并研究印泥成分和印迹在纸张上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特征,又是鉴定中国画作品的一条重要途径。沿着以上三条途径,可以用光学仪器检测到历代中国画作品材料方面的深层信息。不同时空的作品会有不同的材质特征,一方面是书画材料本身的物质成分和微观形态不##一样,另一方面是随着时间推移导致纸、绢、墨、色、印迹发生了变化。通过大量检测历代中国画材质的有关信息,可以掌握各时期中国画材质的共性与特点。如果在鉴定工作中发现某中国画作品的纸、绢、墨、色、印泥以及胶矾等添加剂的材质特征与作者署名及创作年代信息不相称,就可以判定作品有问题。例如:古代作品的墨色中不会含有近现代才有的丙烯色等化学类绘画色。再例,中国画颜料中的普兰即是普鲁士兰,它传入中国的时间就可以成为断代的鉴定依据。实践证明:只要检测出中国画材质与作者署名、作品年代不符的一项“铁证”,就可以否定该作品的真伪。这种通过“科技检测识别系统”寻找“铁证”的方法,颇具学术价值和“实战”作用,它往往是一锤定音的##方法。但是,科技检测识别的方法并不能解决中国画鉴定中的所有问题。后人用老纸、老墨等老材料制作的高仿品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特别是遇到与原作同时期的赝品,以科技检测识别的方法辨别真伪就会倍感困难。好在流传至今的此类作品已极少,而且也有文物价值,并无多大社会危害。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实施的##科研项目:“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已于2010年12月通过验收,顺利结题。目前其科研团队仍在继续深化这项研究,正在根据所汇集并检测的绘画材质成分研究其谱系关系,探讨断代鉴定的时空坐标。该科研团队在书画科学鉴定、科学备案方面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已取得了多项##专利,得到了业内专家们的一致##和称赞,并于2012年获得了文化部第四届创新奖。
在中国画作品鉴定方面尤其要“须知”与“须思”的是:在中国画赝品泛滥成灾的当下,特别是中国画鉴定方面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本来就不多,而今有的已去世,有的年高体衰,他们应对各类赝品的##能力和精力必定是有限的。目前,我国真正称职的中国画鉴定##人员数量并不多,而且由于每一位鉴定专家对中国画的研究都有限,甚至对自己##熟悉的几位画家的作品研究也很有限,因而中国画鉴定工作者发生“走眼”事故似乎必然在情理之中,从而致使中国画鉴定家及鉴定##人员业务口碑不佳。画家及其家属参与鉴定的口碑也不好,也存在明显问题。他们不可能对画家一生中的每一件作品都记忆犹新,偶尔鉴定错某件作品也难免。何况确有一些画家及其家属别有用心,故意不承认自家的作品,被人戏称为“掐死自家的孩子”。因此有人要问,在当下专家鉴定、画家本人鉴定、家属鉴定都备受质疑的情况下,鉴定家、作者、家属都想说了算,到底应该谁说了算?我的回答很简单,证据说了算。书画鉴定之路应向司法办案之路靠拢,也要重证据。一件书画作品被鉴定为真,需要证据。被鉴定为假,也要有证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书画鉴定实践中缺少“科学取证”的环节,就容易出现鉴定错误。现行的书画鉴定个案进入司法鉴定体系时,往往由于缺少了“科学取证”则无法与“重证据”的法律原则相匹配,因而就很难得到司法##。只有重证据,才能让人信服。